中医临床中“风药壮气”的运用与体会
- 健康知识
- 2024-05-27
- 385
风能壮气即风药壮气之义。此云据是承其师叶熙春之应用经验,叶氏之应用,渊源于东垣学说。风药壮气临床应用颇具深意,现作如下讨论。
01
风药的含义与特点
风药是指具有祛散风邪作用的一类药物。从其功效、主治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疏散外风类,多见于解表药与祛风湿药中。二为平息内风类,即见于平肝息风药中。故风药有祛外风与平内风二类,我们讨论的“风药壮气”多指祛外风类风药的壮气之功。
风药的特点大致有四:其一味辛性温,能温能升。其二升阳益气,益胃健脾。其三通泄肝气,疏散风邪。其四祛风胜湿,活血通络。风药的这种温散、升阳、主动、祛湿的特点,与补气药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如皆为阳药,同是动药。根据同气相求、相辅相成之理,以及补气药与风药的特殊关系致使它们有相互为用的作用原理,其中“风药壮气”在临床上为我们开拓了新思路。
02
风药壮气的临床效用
壮气,为壮益正气。风药壮气,是用风药辅佐补气之品,从而增强补气效能的一种方法。临床效用大致如下:
1.鼓舞气血,益气养正
补气方中加风药,则鼓舞气血,使正气旺盛,随风药之鼓荡,以托邪外出。如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方中黄芪益气固表,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以增强益气固表之功,更添防风,鼓舞气血,托邪外出。故本方专治表虚自汗、易受风邪者。柯琴云:“防风遍行周身,称治风之仙药,又为风药中之调剂,治风独取此味,任重功专矣。黄芪能补三焦而实卫,为元府御风之关键,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功同桂枝,是补中之风药也,所以防风得黄芪,其功愈大耳。”因此,黄芪与防风相伍,补气、祛风之功大增。效如此方者尚有王清任之黄芪赤风汤之类。
2.补不碍邪,正气自安
体虚复受风邪,当补虚益气与祛风达邪并进。若一味补气则气壅邪滞,正气愈虚,邪气越盛。此时风药与补气药同进,使风药祛邪,邪去正气自安,复以风药壮气则补气之功愈峻,故亦不碍邪,正气自安,此“风药壮气”之含义更深了一层。如败毒散(《小儿药证直诀》)专治体虚感风寒湿邪、邪正交争、正虚不能敌邪之证。方中用人参补气,使正气足则鼓邪外出,同时配以风药羌活、独活、柴胡之属,一以祛散风寒湿邪,使邪去正自安。二以助人参使之补而不壅。故《医方考》曰:“培其正气,败其邪毒,故曰败毒。”
03
风邪得解,正气自安
风中经络,口眼歪斜,舌强难言,手足不利,多由元气素虚,风邪乘虚而入,气血痹阻,络道不通而致。因此“风药壮气”之义在于祛络中之风,则气血流畅,气自壮,风自灭也。如大秦艽汤(《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专治风邪初中经络之证。方中以秦艽、羌活、防风、白芷、细辛祛风散邪,又配以八珍补气养血,同时配以针对风邪化热的凉血清热之品,因此风邪得解经络自通,正气自复,故汪昂称之为“六经中风轻者之通剂。”
04
补气祛风,相反相成
风药多辛温香燥、辛温发散,故重用久用有耗气伤阴之弊,如东垣云“诸风之药,损人元气”,然而用之得法,并无损气之害,却具有壮气之功。査东垣之书重用风药益气升阳以止泻,用风药胜湿,风药燥湿,风药通阳,等等。这似乎是矛盾,其实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补气祛风的相反相成之义。
补气药与风药的相反相成之妙用在于二者用药之比例和用药之多寡。临床上要达到相反相成、风药壮气的目的,风药宜少不宜多,宜轻不宜重,补气养气之品宜大不宜小,但需视其正邪决定轻重。东垣示范云:“少气不足以息,服正药(补中益气汤)二三服;气犹短促者,为膈上及表间有寒所遏,当引阳气上伸,多加羌活、独活,藁本最少,升麻多,柴胡次之,黄芪加倍。”从中可以领悟到临床上尚需灵活变通。
有时需风药多,有时需补气药多,如前述败毒散中人参需少少与之。《内经》有“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之明训,对于补气药与风药的权衡侧重,我意当可宗尚此意,尤其在五脏气虚证的治疗中若能善于将风药少少与之,供其拨动之力,取其因势利导之功,所谓“四两拨千斤”也。如脾气虚致泄泻加防风、徐长卿,肝气虚加细辛、防风,肾气虚加防风、独活,肺气虚加升麻、白芷,心气虚加桂枝、防己等等,较纯用补气之品其效更著。因此“风药壮气”有它特有的临床价值,值得重视和应用。
一、风药的含义与特点
风药是指具有祛散风邪作用的一类药物。从其功效、主治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疏散外风类,多见于解表药与祛风湿药中。二为平息内风类,即见于平肝息风药中。故风药有祛外风与平内风二类,我们讨论的“风药壮气”多指祛外风类风药的壮气之功。
风药的特点大致有四:其一味辛性温,能温能升。其二升阳益气,益胃健脾。其三通泄肝气,疏散风邪。其四祛风胜湿,活血通络。风药的这种温散、升阳、主动、祛湿的特点,与补气药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如皆为阳药,同是动药。根据同气相求、相辅相成之理,以及补气药与风药的特殊关系致使它们有相互为用的作用原理,其中“风药壮气”在临床上为我们开拓了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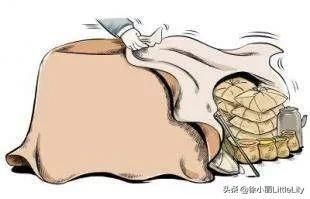
二、风药壮气的临床效用
壮气,为壮益正气。风药壮气,是用风药辅佐补气之品,从而增强补气效能的一种方法。临床效用大致如下:
1.鼓舞气血,益气养正
补气方中加风药,则鼓舞气血,使正气旺盛,随风药之鼓荡,以托邪外出。如玉屏风散(《世医得效方》),方中黄芪益气固表,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以增强益气固表之功,更添防风,鼓舞气血,托邪外出。
故本方专治表虚自汗、易受风邪者。柯琴云:“防风遍行周身,称治风之仙药,又为风药中之调剂,治风独取此味,任重功专矣。黄芪能补三焦而实卫,为元府御风之关键,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功同桂枝,是补中之风药也,所以防风得黄芪,其功愈大耳。”因此,黄芪与防风相伍,补气、祛风之功大增。效如此方者尚有王清任之黄芪赤风汤之类。
2.补不碍邪,正气自安
体虚复受风邪,当补虚益气与祛风达邪并进。若一味补气则气壅邪滞,正气愈虚,邪气越盛。此时风药与补气药同进,使风药祛邪,邪去正气自安,复以风药壮气则补气之功愈峻,故亦不碍邪,正气自安,此“风药壮气”之含义更深了一层。如败毒散(《小儿药证直诀》)专治体虚感风寒湿邪、邪正交争、正虚不能敌邪之证。方中用人参补气,使正气足则鼓邪外出,同时配以风药羌活、独活、柴胡之属,一以祛散风寒湿邪,使邪去正自安。二以助人参使之补而不壅。故《医方考》曰:“培其正气,败其邪毒,故曰败毒。”
三、风邪得解,正气自安
风中经络,口眼歪斜,舌强难言,手足不利,多由元气素虚,风邪乘虚而入,气血痹阻,络道不通而致。因此“风药壮气”之义在于祛络中之风,则气血流畅,气自壮,风自灭也。如大秦艽汤(《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专治风邪初中经络之证。
方中以秦艽、羌活、防风、白芷、细辛祛风散邪,又配以八珍补气养血,同时配以针对风邪化热的凉血清热之品,因此风邪得解经络自通,正气自复,故汪昂称之为“六经中风轻者之通剂。”
四、补气祛风,相反相成
风药多辛温香燥、辛温发散,故重用久用有耗气伤阴之弊,如东垣云“诸风之药,损人元气”,然而用之得法,并无损气之害,却具有壮气之功。査东垣之书重用风药益气升阳以止泻,用风药胜湿,风药燥湿,风药通阳,等等。这似乎是矛盾,其实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补气祛风的相反相成之义。
补气药与风药的相反相成之妙用在于二者用药之比例和用药之多寡。临床上要达到相反相成、风药壮气的目的,风药宜少不宜多,宜轻不宜重,补气养气之品宜大不宜小,但需视其正邪决定轻重。东垣示范云:“少气不足以息,服正药(补中益气汤)二三服;气犹短促者,为膈上及表间有寒所遏,当引阳气上伸,多加羌活、独活,藁本最少,升麻多,柴胡次之,黄芪加倍。”从中可以领悟到临床上尚需灵活变通。
有时需风药多,有时需补气药多,如前述败毒散中人参需少少与之。《内经》有“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之明训,对于补气药与风药的权衡侧重,我意当可宗尚此意,尤其在五脏气虚证的治疗中若能善于将风药少少与之,供其拨动之力,取其因势利导之功,所谓“四两拨千斤”也。如脾气虚致泄泻加防风、徐长卿,肝气虚加细辛、防风,肾气虚加防风、独活,肺气虚加升麻、白芷,心气虚加桂枝、防己等等,较纯用补气之品其效更著。因此“风药壮气”有它特有的临床价值,值得重视和应用。
风之为物,惟恍惟惚,缥缈变化,来去无踪; 微兮狂兮,不解其性,微则渺茫乾坤大,狂却猛烈崩山石;寒兮暖兮,难明其理,寒则瑟瑟凋秋叶,暖却和煦发万物。
对于风药的功效记载,最早可追溯到马王堆医书,其后早期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对风药都有详细的论述。从汉至隋唐之前,有关风药的论述多散见于各家本草著作中,少有详细的方书记载。到了隋唐时期,风药的临床运用如雨后春笋一般,林林总总见于当时诸多临床书籍。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孙思邈的《千金方》。那么到了宋代,集诸家方剂之大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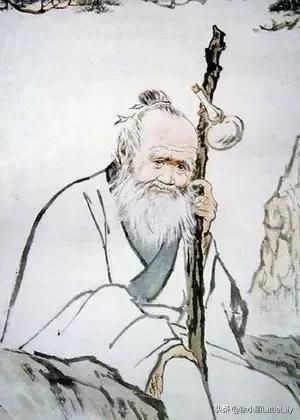
金元时期,是风药临床运用的顶峰,同时也是风药临床运用走向衰落的转折点。“风药”之名,即出于金代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张氏首创“药类法象”理论,取法天地五运之象,谓“药有气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主治之法,各各不同。”其中“风升生”一类为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列有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细辛等20味,可谓后世风药之滥觞。

其弟子李东垣则进一步提出“风药”之名称,并将风药广泛地运用到内伤脾胃的治疗上。其中包括了至今在临床上都十分常用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等。自此,“风药”一词遂为后世所常用,而且包含的药物逐步有所增加。 但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这类药物被广泛地运用,风药耗气伤津的副作用,逐渐的显露出来。朱丹溪首先对风药的滥用做出了批判,其看法对于中医的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于养阴填精之法又有十分精到的见解,以至于造成了明清时代治疗方法和用药向柔腻养阴的方向转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动了清代温病学派的兴起,导致了滋阴清热的用药方法大行于世。而历史总是呈现出矫枉过正的趋势,因此清代以后的医家们视风药和经方中的麻黄桂枝等温热药物为虎豹。才会出现如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生平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的错误论断。这种用药风气延续到了清末民初,当时编写的新式中医教材,同样继承了温病学家们的偏见,对于风药的运用也视为畏途。新中国成立之后,继承了民国时期新式中医教材的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则犯了同样的错误。竟然将风药矮化并简单归纳为祛风解表的药物,毫无疑问,这并不是风药的本来面目。
在临床中见识了风药的运用之妙,在诸多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结合自身数十年的经验,深入地讲述了他对于“风药”的认识。
怎么对于风药能够有认识?这是因为有事实把我逼的。举一个例子,我那儿子半岁的时候拉肚子,因为没有及时地看,我都忘了为什么引起拉肚子,反正拉肚子拉了半个月也看不好。后来拉得都坐不住了,我也没办法。我用了咱们常用的这些方子什么“参苓白术散”了,这些正规书上头说的这些,没有一样管用的。最后没办法了,用那个“理中汤”,还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翻开了那个李东垣的《脾胃论》。把他那里面的药凑合了几样,因为我不太懂那个道理,我看他治拉肚子全都用风药,所以我就把他那个药,羌活、独活、防风就拿出来四五样,甘草,只是简单的四五样药,那小孩也吃不了多少药,我捏一点点,给他一煮,二三调羹勺,一喝以后他第二天就不拉了,立即就停止。后来,总共可能就是喝了一次或者两次,反正他那个病就再也没拉。虽然我把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因为不理解病机,所以我也没有推广,也没有总结,也不会总结。对于《脾胃论》可以说是看不懂,只是表面上的文字似是而非。后来又碰见了几个类似的病,老是治不好,实在没招了,我就用这。有一个肚子疼的,没招了,我就用李东垣的方子,一治他也好了。还一个胸疼的人,我用那个胸痹那一类方那就无效。最后还是用风药治好的。当时我都用风药治好了好多例子,但是我都藏在内心里头,从来没给人宣传。因为从内心里头我存在着疑问,我觉得这是最后没办法的一招,不一定是普遍的规律,我当时不是这样认识的。
咱们这是基层的医生有一个特点,人家病人能来,用满怀期望的眼神儿看着你,你一次失败,不要紧,你再来,你十次失败他还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哈哈哈。你说你咋弄,对吧?哎呀,他就对你相信。他说“你看孙大夫,我知道你这人诚实不骗人,你给我研究研究,总有办法嘛。不就这么大个病嘛,对吧?我相信你,诶,我不埋怨你,你就给再想办法。”有的最终还是没治好,嗨。我现在还经常说起一个病例,有一个肚子胀病人,我始终治不好,哎呀,费劲了。那个肚子胀病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存在了一二十年,那个病,把他的脉象啊,形象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直期待有一天看书或者触类旁通或者别人给我一传,豁然开通,有那么一天能治好他。后来真的有一天我想通了!我从李东垣那个道理上开通了,我知道要升阳就要靠风药,风药者是春也。他是人与天地相应,你人体里面,你泻就是冬,对吧?你要这个发,你就是春,就是风药,才能发。所以,我那个时候把那个肚子胀没治好,他要是现在再来的话我一定给他治好,我心里很欣喜。
从这以后呢,我就在这方面就注意了。把《千金方》又拿出来了,哈哈。积满灰尘的《千金方》,我拿出来拍一拍,哎呀,我这个时候才知道,咱们老孙家人还是有能力的,就是呀,但那个时候咱不理解嘛,对吧?为了研究风药的,我就找《外台秘要》。因为《千金方》有一个缺点:不说这些药的来源,不说方的来源。《外台秘要》的好处在于它下面都注着来源。可是当时我没有《外台秘要》,所以光为了这我到西安去了几次,到陕西中医研究所借的书,当时回来好一部分还是影印的、复印的、手抄的,把它那个总结了一遍,下了一顿苦功夫。从这以后我就对于风药有了一个理论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拉肚子治不好。古人怎么治?你只要看一看《寓意草》上面那个喻嘉言,他有一个逆流挽舟法,就是“败毒散”。“败毒散”就是风药,它起的作用就是就是生发,让脾气往上走,一走他就不泻了。他那个案很精彩,我相信喻嘉言他对这个“败毒散”理解是学有渊源。中医就是呀,几千年人家一代一代,他都有他的渊源,他不会是他个人想出来的,突发奇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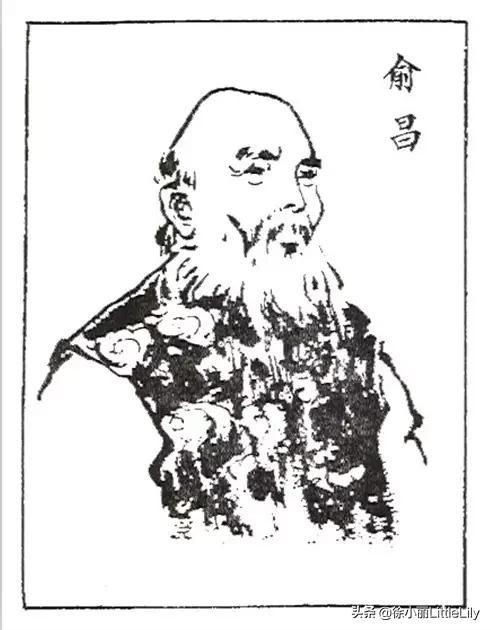
“败毒散”作用点在于脾胃。它其实是在胃上,从脾胃上往上发的。风药有广泛地用途。你比方说是胸痹,当时疼得不行,几味风药就立刻可以止住。它用通经络,就是羌活独活加上川芎啊,如果他大便不稀的话就加上当归、甘草这一类的药,川芎,马上就可以去,它的用处极其广泛。你以后就可以注意一下,我在一些书上就会提到这一点。现在的人实在不知道风药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中医的主流。
1.
>>>风邪的治病特点>风药的定义>常用风药的分类>风药的特性>风药的禁忌
发表评论